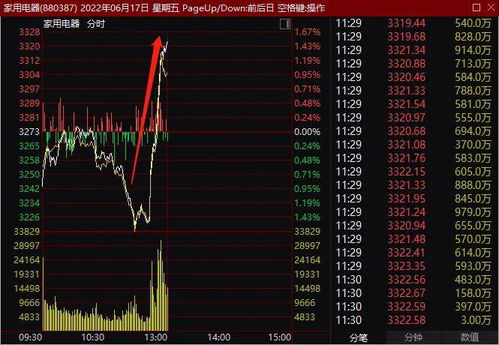学术
学术
作 者:孙佑海、朱炳成
编 辑:亚峰
编者按
本文刊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现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推送。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摘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实施是降低环境健康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为人体健康提供有效保障。美国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管理,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并使得该制度成为美国环境立法和制定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美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包括危害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步骤。同时,通过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者的有效衔接,实现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性。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频发发生,导致的环境健康问题日益严重。而保障人体健康作为我国环境法制目标之一,尚未得到有效重视,缺少法律保障基础。基于我国环境健康规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可借鉴美国风险评估制度经验,从贯彻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健全风险评估制度、完善企业环境健康管理体制和推进多元化公众参与模式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法律制度。
关键词
环境健康;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制度;法律制度
我国经济领域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凸显。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9条要求国家建立和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但对环境风险评估的法律地位和实现机制等问题并未作出规定,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仍处于空白状态。美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的成功经验,说明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是有效降低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我国建立健全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概述
(一)环境健康的概念界定
1989年《欧洲环境与健康宪章》(下文简称“宪章”)(European Charter on Environment and Health)中将环境健康定义为由环境要素所决定的人类健康和疾病。该宪章认为环境健康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峻,并非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问题,应该实现国家间协同合作模式。但是,该宪章中关于环境健康概念的解释仍然较为宽泛并未对环境健康进行较为严格的定义和范围界定。目前,关于环境健康的定义和范畴有多重观点,一种观点即是“宪章”中对环境健康的定义,另一种观点则扩大了环境健康的范围,认为环境健康主要是指由化学、辐射和生物等媒介引发的疾病。与此同时,环境健康应更广泛地考量物理、社会和美学环境等要素,具体包括房屋、城市发展、土地使用与流转等方面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本文所称环境健康,是指因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或危险。[1]
(二)风险评估的界定与发展路径
风险(Risk),是指“遭遇危难、受损失或者伤害等之可能或者机会”。从安全科学上讲,风险是特定危害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本文所称的“风险”,是指因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行为对人体健康或者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可能性。预防(Precaution)是指“事先采取的避免危害或者风险之行动”。作为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将“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定义为遇有严重或者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
风险评估制度作为美国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它是基于对流行病学的数据和动物实验结果对剂量和反应的显示而发展起来的。起初,美国联邦政府采用风险评估的目的并不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驱动,而是在于风险评估可以使得他们在没有直接的证据的前提下可以回答和解释相关问题。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环境风险评估制度的确立和迅速发展得益于时代性。[2]1976年,根据从动物实验中获取的剂量反应曲线,建立了一些应用于评估人类癌症风险的数学模型。[3]这期间,美国环保署一直依赖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相关物质的毒性,并未试图采取定量的方法来检测暴露中的环境风险程度。至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国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官员仍表示,美国尚不具备充分合理的科学基础运用风险评估来制定监管决定。[4]
美国风险评估制度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环境保护运动日益受到关注的社会形势下,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诉美国石油协会一案中,法院判决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所制定的更为严格的苯暴露标准是违法行为,因为其未能给出实质性证据,以证明遵循更为严格的标准对预防癌症具有明显的作用。联邦行政机关很大程度上将该案件解释为需要依据定量风险评估,甚至在其有效性存疑的情况下仍需考虑将风险的量化作为进行决策的工具。[5]
尽管随后里根总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所有法律法规都需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意味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所有启动规制行为的前提是潜在的收益明显高于规制成本。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确要求对新制定法律法规要进行风险评估,但与其他替代性监管手段而言,该命令所提及的风险的数值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法律法规效益的定量化。
美国风险评估制度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发生于1983年,时值威廉·洛克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任美国环保署署长。洛克肖斯接任美国环保署署长时,正逢环保署限于科学可信度饱受质疑之时,他认为风险评估是环保署重新在获得公众信任的有效方法。并且,由于定量风险评估为风险评估主管机关带来了巨大的资源需求,从而使得其减缓了评估主管机关实施监管工作的步伐,亦推动了里根总统关于减少政府监管的政策。
如今,美国环保署与其他联邦和地方环保机关都将风险评估应用于多种监管决策之中。美国环保署将环境风险评估用来甄别环境中对人体健康风险的危害程度和类型(例如:居民、工人以及游客等),以及环境中化学污染物和其他压力源对生态接收者(例如:鸟类、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等)的危害程度和类型。美国环保署通常将环境风险评估应用于人类健康和生态两个领域。其中,环境风险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1)环境介质(例如:土、气和水等)中化学成分的含量;2)人体与受污染的环境介质的接触程度;3)该化学物质的固有毒性。[6]
二、风险评估的法律基础
风险评估作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其在美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危险废物管制领域。风险评估最早被应用于量化化学物品可能具有的毒性,并进行人体暴露评估,最后由政府确定其认为安全的数字监管阈值。本部分从成文法和普通法两方面,阐释风险评估行为的法律基础及美国环境法律法规和判决中关于风险评估的具体规定或解释。
(一)成文法依据
随着美国环境法律的立法模式和方法的发展,风险评估方法在美国环境立法中的角色亦从次要辅助地位逐渐转变为主要立法工具之一。目前,美国环保署和其他联邦及州环境保护机关都已将风险评估广泛地应用于决策之中。其中,用定量风险评估来决定一个行为或者化学品是否安全,或者该行为或者化学品具有的危险是否为可接受或严重的,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应用定量风险评估的形式。例如,美国环保署已经将风险评估应用于《安全饮用水法》中饮用水所含致癌污染物的等级设置、《清洁水法》中工业企业向地表水排放致癌物质的等级设置、《资源保护和恢复法》中有害废气物的定性、《清洁空气法》中要求经营者根据最佳可获得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安装设备后的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的等级设置等。同时,美国环保署也将风险评估应用于超级基金项目的特定废弃场所清理的审批之中。[2]
风险评估与致癌物质的规制。以与环境风险评估密切相关的致癌物质规制为例,据统计,美国有约21部联邦法律对致癌物质进行规制。其中涉及到的监管主体包括美国环保署、美国职业与健康管理局(OSHA)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等在内的约12个行政机构。[7]根据规制标准的不同,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也有所不同。[8]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以技术为基础的标准模式。原则上以技术为基础的标准是与定量风险评估无直接联系的。[9]例如,《清洁水法》规定美国环保署需要基于最佳实用技术(Best practicable control technology currently available, BPT)来制定统一的工业排放限值,如果美国环保署从科技和经济可行性角度认为消除所有排放的污染物是可行的,则可要求消除所有排放的污染物。尽管上述规制手段与量化风险评估并无直接关联,但是其仍可被应用于显示使用科学技术后对人体暴露的特定风险程度以及计算剩余风险。[8]42又如,美国《清洁空气法》1970年修正案中要求美国环保署确定有毒污染物并制定相应的标准,使得环境标准达到适当的安全范围,以保障公众健康。但是,直至1990年美国环保署仅明确了8种物质为有毒污染物。面对数以千计的可能引起危害的物质,这无疑是美国环保署在执行环境法律中的一个失败。为此,《清洁空气法》1990年修正案直接规定美国环保署需要根据最佳可获得技术为国会认定的每一种有毒污染物制定排放标准。同时规定美国环保署可以应用风险评估方法删除国会所列的有毒物质清单中个人暴露风险小于10-6的物质。[9]可见,此时风险评估制度在美国环境立法中仍处于次要位置。
其次,“零风险”标准模式。一些美国环境法中要求通过控制技术将风险降为零。例如,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中规定的德莱尼条款(Delaney Clause)。该条规定针对食品添加物,应完全禁止有致癌可能的食物添加剂。此时,风险评估的作用可能仅仅是证明风险尚未符合标准,即仍然存在风险。[8]但是,随着美国《食物质量保护法》的通过,“零风险”标准被统一的可忽略风险标准所替代,[10]该标准规定如食品添加剂的终身致癌率为百万分之一,则可忽略其风险。[11]
最后,以风险为基础的治理标准。目前,除了超级基金修复体系外,美国多数州都采用了基于风险管理之方法治理土壤污染。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该州将基于风险管理解释为通过风险管理实现土壤目标修复水平。并且,该州于2003年制定了《基于风险管理的矫正行动》(Global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简称Global RBCA)。该法案规定,基于风险管理的矫正行动,是指以针对暴露的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影响而实施的救济行动为基础的整个过程,该行动适用于佛罗里达州所有的污染场地。在诸如石油产品污染场地和棕色地块区域等的计划场地,基于风险管理的矫正活动是基于默认的前提和场地的特定数据,为各种化学物质建立污染物目标修复标准(contaminant target cleanup levels, CTLs)和以风险为基础的目标浓度。[12]可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在该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决定着污染场地的治理程度,以及该场地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等关键问题。
(二)普通法依据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尚未明确定量风险评估方法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并且,亦未有明确的美国环境法律对风险评估进行授权性规定。这就使得,风险评估实践的法律基础更多的来源于美国法院的司法判决。[9]
如前所述,对于风险评估制度的发展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案件之一,即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诉美国石油协会(Industrial Union Dept., AFL-CIO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一案。该案的起因是由于OSHA在进行了关于苯暴露与白血病的关系评估论证后,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工人可接触到的苯暴露标准。具体为,OSHA将工作场所中苯暴露量从百万分之一(ppm)10份降低至1 ppm。而该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OSHA是否有权制定该标准,该标准的制定是否超越了国会的授权。案件审理过程中,OSHA认为,他们制定这样的标准是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来评估苯暴露量和工人患癌之间的关系。但是,OSHA仅将上述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定性,并未进行定量风险评估,研究结论的目的是支持该标准的合理性。但在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该标准无效,并将该案发回重审。判决意见中,史蒂文斯大法官认为,如果OSHA根据《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认为该标准是合理的,并且符合科技与经济可行性,则需要证明目前工人的工作场所是不安全的。同时,史蒂文斯大法官解释道:“安全并不意味着零风险,是否安全需要主管机关提交一份阈值证据,证明显著风险的存在,并且该风险可以通过执行该暴露标准而得以降低或者消除,但OSHA并未能提交上述证据。”但是,史蒂文斯大法官在其意见中认为,在评估风险需要法律进行有效规制时,定量风险评估的使用是必要的。
关于公共公民组织诉泰森一案(Public Citizen Health Research Union Group v. Tyson)。如果说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诉美国石油协会一案中定量风险评估的法律地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在公共公民组织诉泰森一案中,消除了关于风险评估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该案是时隔六年后,OSHA制定的化学物暴露标准再次受到质疑的典型案件。该案中,OSHA在通过大量动物实验研究基础上制定的环氧乙烷暴露标准受到质疑。此时,OSHA吸取了在苯暴露标准中的教训,通过运用数学模型进行量化风险分析,并且配合一系列的保守性假设来推断由动物到人体的数据以及预测人体的接触程度。通过上述计算和分析,OSHA认为,如果法规允许工人暴露于浓度为百万分之五十的环氧乙烷中,则会发生634至1093个工人因接触环氧乙烷而死亡的事件。OSHA认为从安全角度而言,这个死亡数量是过高的。之后,OSHA又证明,如果将环氧乙烯的暴露量从50 ppm降低至1ppm,则死亡数量将仅为12到23个。本案中法院支持了OSHA制定的环氧乙烷的暴露标准,上诉法院认为本次OSHA在修改化学品暴露标准的过程中,符合在Industrial Union Dept., AFL-CIO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一案中最高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提供证据和说明的要求。并且,OSHA制定环氧乙烷暴露标准的过程与制定苯暴露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案中OSHA提交了充足的证据,有效的论证了风险程度。
上述两个案件在法律上确认了对定量风险评估方法的认可。那么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诉美国环保署(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EPA)一案中,则体现了风险评估方法亦可作为支持或者反对法规的依据。该案涉及到EPA根据《清洁空气法》第112条制定氯乙烯排放标准问题。《清洁空气法》第112条规定美国环保署在制定排放标准时需要为公众健康提供足够的安全范围。而EPA则将该条解释为法律授权其证明现有的氯乙烯标准可能产生的损害,从而根据最佳可获得技术有权制定更低的标准。而在这个标准中则几乎不会涉及到风险评估的方法。上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审理的劳工联合会一案的判决认为,EPA错误地解释了《清洁空气法》中关于授权EPA识别损害等级这一问题。联邦机关需要通过如下两个步骤进行识别:第一步,EPA需要运用定量风险评估的方法识别一个具体的氯乙烯排放安全浓度值。同时,法院也认为安全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从而要求EPA作出第二步,即EPA可能需要考虑风险评估的内在局限性,以及关于人体暴露于致癌物中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有限的科学知识。并且,上诉法院明确了EPA在进行第二步时允许使用的方法。
上述三个案件均是在不考虑风险评估中存在的科学不确定性的前提下,进行审理的。基于该前提,上述三个案件的审理结果均认为定量风险评估是制定法规和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美国环境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后续案件审理中,亦愈发重视风险评估中包含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不能单一的将其作为立法和决策的基础,亦需考虑其他相关问题和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立法和决策,诸如由于“科学不确定性”而无法定量风险评估的问题,以及效益分析方法作为立法和决策基础的合理性。
三、 风险评估制度的构成要素
环境决策中主要应用的风险评估包括定量风险评估和比较风险评估两种。其中,定量风险评估是美国环保署在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中应用较多的一种,其具体程序包括:危害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步骤。同时,风险评估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降低风险的发生。
(一)风险评估类型
美国应用于环境决策的风险评估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定量风险评估与比较风险评估。所谓定量风险评估,是指通过检测一种行为或者某种环境介质,并试图将由于暴露在行为或者有害介质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和危害进行定量的评估方法。与之相对应的比较风险评估,则是指通过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风险程度进行排序的过程。其中,定量风险评估是美国环保署一般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2]
定量风险评估最常用也是最饱受争议之处,即是将其应用于决定一个行为或者化学制品是否“安全”或者用其决定由于该行为或者化学制品所产生的风险是否处于“可接受”或者“显著”的程度。例如,美国环保署根据《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案》(FIFRA)运用定量风险评估来规定食物中杀虫剂残留等级;根据《安全饮用水法》运用定量风险评估来规定饮用水中致癌污染物等级;根据《清洁水法》运用定量风险评估来规定工业企业排放到地表水中致癌物等级等等。[2]
(二)风险评估程序
在进行风险评估前,美国环保署需先制定规划(Planning)以确定风险评估的目的、范围和使用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规划是有效进行风险评估的前提。美国环保署所采用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标准程序包括危害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步骤[6]。
1. 危害识别(Hazard Identification)
危害识别,是一个定性评估的过程。在化学压力源的情况下,该过程通过检测给定化学物质(或一组化学物质)的可用科学数据,并产生一定权重的证据来表明负面影响与化学试剂之间的联系。危害识别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由于某些物质的暴露而产生的负面健康影响的类型。其中,暴露的压力源可能对人类产生许多不同种类的不利影响,如疾病、肿瘤、生殖缺陷和死亡等。实践中,美国环保署和其他联邦机关负责通过对压力源与人体健康或者生态系统是否具有潜在危害进行识别,以及如果存在潜在的危害,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危害等问题进行识别。
美国环保署在进行危害识别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获取数据。第一类是人类临床学研究,通过对统计过程进行控制的方法分析研究结果,为证明压力源(通常为化学物质)与产生负面影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佳证据。然而,因为人体环境危害测试关系到严重的伦理问题,所以类似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不能使用。第二类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涉及到人口统计和评估,用以检验暴露的压力源与人类健康影响是否相关。该研究的优点在于研究对象包括了人类,缺点在于这些研究通常布局在有准确的暴露信息的地方以及难以分析出多种压力源的影响。第三类是动物研究,当违背伦理的人类研究数据不可用的时候,只能依赖来自动物研究的数据推断压力源对人类的潜在危害。因为动物实验可以被设计和控制,通过进行动物实验弥补特定数据的空白。但是,仍存在从动物实验受试者外推到人类相关结果的不确定性。
2. 剂量反应评估 (Dose-response)
剂量反应评估,是指对人体暴露于少量浓度的化学品时风险增加几率的量化分析评估。该评估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暴露程度的情形与产生不良健康反应的概率比,以及剂量的增加与风险增加之间的关系,即证明剂量与毒性反应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这项研究是在通过大剂量动物实验的同时,纳入一系列旨在增加数值结果保守性的假设,从而证明剂量与毒性反应直接的关系。剂量反应关系表明了不良健康反应产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以及与暴露在不同剂量和条件中的药剂的关系。该原理亦被应用于浓度反应关系研究中。“暴露- 反应”关系可用于描述剂量反应或浓度反应或其他特定暴露条件。
通常情况下,随着剂量增加反应几率也会随之增加,较低的计量通常不会产生任何反应。一定程度的剂量下,反应开始在所研究群体的一小部分中发生或以低概率发生。但是,出现反应的剂量以及随剂量增加而增加的反应几率,在不同污染物、个体和暴露途径等之间是可变的。并且,剂量反应关系的形态取决于试剂。反应的类型(肿瘤,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等)和实验受试者(人或动物等)。可见,剂量反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毒性研究通常被应用于检测数量有限的不良反应。
3. 暴露评估(Exposure Assessment)
暴露评估,是指测量或者估计人类暴露于环境中某种物质的程度、频率和持续时间,或评估尚未释放出的物质在未来暴露程度的过程。暴露评估的目的在于计算暴露或者剂量的数字估计值。暴露评估包括对暴露于物质中的人群的范围、性质和类型的一些讨论,以及对上述信息中的不确定性的讨论。
首先,确定测量方式以及剂量种类。暴露可以被直接测量,但更常见的是通过根据所测量的环境中该物质的浓度、化学品运输方式,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摄入量进行间接估计。暴露评估过程中涉及到不同种类物质的剂量。暴露评估将同时考虑暴露路径(物质的来源以及人体接触该物质的路径)以及暴露途径(物质进入人体的途径)。暴露途径通常进一步描述为摄入(通过身体开口摄入,例如作为进食、饮用或吸入)或摄取(通过组织吸收,例如通过皮肤或眼睛)。
其次,明确暴露的范围。对于任何具体的物质或者场地,都有个体实际接触暴露物质的范围。一些个体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与暴露物质接触的程度较高(例如:工厂工人接触工厂中暴露的化学物质)。其他一些个体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少量地接触到了暴露物质(例如:个体在某个工厂的下风向位置进行娱乐活动时会短暂地接触到暴露物质)。美国环保署风险评估政策要求评估机构在进行暴露评估时需要考虑到一系列可能暴露的水平。常见的可能产生的暴露,主要包括“集中趋势”与“高端”暴露评估两种。“集中趋势”暴露,是指基于该物质在环境中暴露的程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而对受影响人群的经历进行一个平均值的估计。“高端”暴露,是指一些个体所经历过的最高剂量的评估,通常表示为约等于个体暴露范围的第90百分位数。
最后,量化暴露风险。量化暴露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是接触点测量法,即在发生暴露时在接触点测量暴露程度。测量内容包括暴露的浓度和接触的时间,进而将将二者进行整合;二是情景分析法,即通过单独评估,保留浓度和接触时间,最后将两方面信息相融合以评估暴露程度;三是重建法,即在暴露发生后,可以通过剂量对暴露风险进行评估,主要通过内部指示物(例如:生物标记、体内积存量和排泄水平等)进行重建。
暴露评估本身就是一个定量风险评估的过程,上述三种量化暴露风险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是基于不同的数据,且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所以,综合运用三种方法是有效增加暴露风险评估可信度的良好方法。
4. 风险特征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所谓风险特征描述,是指风险评估人对风险是否存在、风险的属性、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哪里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政策选择中需要做出判断的信息所作的表达。风险特征描述同时存在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和生态风险评估之中。该步骤的目的在于总结和融合前三步得出风险评估信息,并最终得出一个关于风险的整体性结论。在实践中,风险评估(例如危害评估、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会形成一份单独的风险特征描述,用于表述主要发现、假设、限制因素和不确定性。每份独立的风险特征描述为综合性风险特征分析提供了基础信息。因此,最终的风险特征描述是基于每份独立风险特征描述基础上的综合性分析。
美国环保署的风险特征描述政策要求编写风险特征描述时应遵循如下原则[13]:(1)透明性。特征描述中应充分而明确地披露评估中每个步骤的风险评估方法、默认假设、逻辑、基本原理、外推、不确定性和总体强度。(2)明确性。风险特征描述报告应该易于读者理解,无论是风险评估过程的参与者和未参与人。要求文档简洁,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并且,应该根据需要适当使用有助于理解的表格,图形和方程。(3)一致性。风险评估应以符合美国环保署政策的方式进行和操作,并与美国环保署内部其他范围相似的计划项目中的风险特征描述相一致。(4)合理性。风险评估应基于合理的判断,所运用的方法和假设应与当前尖端科学相一致,并且应该以完整和翔实的方式表述风险特征。这四项原则统称为“TCCR(Transparency, Clarity, Consistency, Reasonableness)原则”。[14]为了在风险特征描述中有效实现TCCR原则,要求将该原则应用于风险评估的每一个阶段的风险特征描述之中。
(三)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之关系
风险管理是评估如何保护公众健康的过程。具体而言,风险管理决定着是否以及如何管理风险,其中需要考虑法律、经济和行为的因素,以及每个决策或者备选方案对生态、人类健康和福利所产生的影响。风险管理行为的例子包括决定企业可向河流排放的污水量;决定哪些物质可以存储于危险废物处理设施中;决定危险废物场地的清理程度;制定排放,储存或运输的许可标准;建立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确定饮用水中允许的污染水平。
风险管理除了基于风险评估为其提供的有关潜在健康或生态风险的信息外,同时需要考虑科学、经济、法律、社会和科技等因素。具体而言,科学因素是风险评估的基础,是指从毒理学、化学、流行病学、生态学和统计学中提取的信息;经济因素是为了使得风险管理者对风险成本和风险控制效益有着更加清晰的认知;法律和法院判决则在确定风险评估机构、制定管理决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确定降低风险的进度、级别或方法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社会因素是指包括收入水平、种族背景、社区价值、土地使用、生活方式和受影响人群的心理状况等在内的可能影响个体或可定义群体对特定压力源的风险的易感性因素;技术因素较多的关注与风险管理方案的可行性、影响和范围等方面;政治因素是基于联邦政府各部门,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甚至与外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践中可能表现为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通过议会议员、特殊利益团体和有关公民进行的质询;公共价值则反映了社会对环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广泛态度。上述这些因素从不同角度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信息支持,为风险管理行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保障。
四、 美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基于我国当前存在环境健康问题,美国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贯彻风险预防原则
美国虽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但在实践中已将风险预防原则的作用通过多项环境法律制度加以确认并予以实施。根据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风险预防原则至少包括四方面内涵:其一,预防的对象包括潜在的风险和现实的损害。损害作为风险发生的现实转化,亦是风险预防的对象之一,因此该原则中将“损害预防”作为内容之一。其二,潜在危害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对于人体健康而言,只要根据现行的法定阈值标准,确认有可能造成损害,即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对于生态环境而言,其危害程度须达到“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程度,才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其三,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在科学上有可能无法判断相应的现代生物技术相关活动是否必然导致危害的发生。这与环境法中的“科学不确定性”特点相吻合。其四,此种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构成反对或者延迟采取损害预防措施的理由。[15]
预防原则作为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与风险预防原则在功能和作用上具有一定相同之处,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是指对开发利用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降或者环境破坏等应当采取的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环境损害。[16]101从该基本概念看出,风险预防原则较之于预防原则具有更强的风险防范性,并且突出了科学不确定性在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的关键性。而预防原则更多的体现了我国环境治理中的“末端治理”方式,实践中该原则亦更多的应用于降低已经产生的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行为的损害范围和程度。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提升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能力,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可见,我国已逐步强化对环境风险预防的重视程度,以扭转原有的事后救济的环境管理模式。但是,就目前已经存在的环境健康问题,该规划中尚未将其纳入风险防控体系之中。而美国作为环境治理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通过将风险评估制度引入政策决定和立法之中,并将风险评估作为行政机关制定环境政策和法规的先决条件之一,较好的实现了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预防。参考美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健康形势,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充分认识人体健康风险预防的重要性,尽早将风险预防原则纳入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中,充分发挥风险评估制度对于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的预防作用。
(二)完善环境标准制度
环境标准,是指为了保护人体健康和社会物质财富,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生态平衡,而就环境中污染物的允许含量、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浓度、时间和速率以及其他相关事项依法制定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制度,是指依法对环境标准进行管理的一整套措施。由此可见,环境标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依靠技术手段制定污染物的暴露标准,从而实现保护人体健康和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目的。环境标准的功能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制定科学的环境标准降低环境污染的发生;事中,环保部门依据环境标准对企业等污染主体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依据环境标准进行处罚并进行生态修复等。
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诉美国石油协会一案中,美国职业与健康管理局未能成功修订环境标准的原因之一即是未进行科学的定量风险评估分析。但在数年后,在公共公民组织诉泰森一案中,依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通过运用定量风险评估方法对原有的环氧乙烷暴露标准导致的死亡率与修订后环氧乙烷暴露标准的死亡率进行对比,为该标准的修订提供了充足的依据,证明了原有暴露标准的风险程度。可见,风险评估制度在美国环境标准制定中的作用,由原有的次要辅助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修订环境标准的必要程序。这亦说明风险评估制度对于美国制定科学的环境标准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尽管我国环境标准制度的概念中涉及了保护人体健康之目的,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难以在现有环境标准之下科学评估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亦使得,我国现行的环境标准与保护人体健康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并且,我国环境保护部门与公共卫生部门间缺乏协调配合,环境标准制度尚未与公共卫生指标相融合,这都对科学评估企业环境污染行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造成困难。为此,建议从如下方面完善我国环境标准制度:
首先,应当基于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科学制定环境标准。为完善环境标准制度,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健康风险评估制度,通过对污染行为影响人体健康的科学评估,合理制定环境标准,从而发挥环境标准制度对环境污染导致人体健康的预防作用。其次,建立环境保护部门与公共卫生部门关于环境健康的联合工作机制,从而完善环境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应将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公共卫生指标吸收到环境标准之中,从而完善我国现有的单一的环境标准。[17]再次,应制定动态环境标准,该动态环境标准应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不同季节的天气情况,以及河流水量变化,及时调整环境标准。针对季节性特征较强的地区,应制定具体的环境标准。例如,根据河流的丰水期和枯水期,在不同水量情形下,应实施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另一方面,借鉴美国环境标准的制定经验,应根据对污染物暴露量的定量风险评估分析方法,及时调整环境标准,实现环境标准对人体健康的有效保护。
(三)健全风险评估制度
基于我国当前环境管理现状,构建科学的环境风险评估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关键。以美国风险评估机制为鉴,建议从如下方面构建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
首先,完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法律基础。我国2007年发布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为建立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框架,该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法律法规体系作为目标之一。但截至目前,我国仍缺少足够环境与健康评估工作的法律依据。完善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法律基础,是构建我国环境与健康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尽快出台规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全面实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
其次,确定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内容和范围。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法律基础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明确环境风险评估制度的内容以及范围。由于我国目前风险评估技术较为薄弱,缺乏系统性研究,因此在确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具体内容方面,建议借鉴美国风险评估制度的成功经验,重视定量风险评估。一是,风险评估前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科学的规划是有效风险评估的前提。规划应当明确潜在的风险承受主体、风险类型、风险发生地点、风险来源、人体对该风险可能产生的反应、该环境危害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以及该环境危害的毒性反应周期等,并确定风险评估的目的、范围和使用的技术方法。二是,明确风险评估流程,即风险评估“四步法”:危害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三是,应将风险沟通机制贯穿于整个风险评估流程之中,使各方利益主体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最后,明确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核心要素,风险管理是基于风险评估提供的一系列信息而采取的管理行动。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不仅有助于实现降低风险发生几率,亦有助于实现生态损害修复人体健康恢复效果最优化。实践表明,对受损害场地的全面修复费用过高,而最佳修复目标的实现则受到周边环境和人群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受损场地用途亦不相同。因此,一味追求最佳修复效果并非最优选择,进而,基于风险管理的修复目标逐步在实践中得以应用。
(四)完善企业环境健康管理体制
企业作为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24、31、32其内部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建设不可忽视。如前文案例所述,美国职业与健康管理局修订环氧乙烷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为了降低工人由于在工作中接触该物质而产生的死亡率。职工健康风险亦是我国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应当在完善环境与健康监管体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在环境健康管理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职工环境健康管理必须强化。
发挥企业在职工健康风险管控中的作用,可以从提高企业环境、健康和安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EHS)管理能力着手,从而强化企业EHS管理的理念。[19]EHS管理是指一个组织或企业通过进行风险分析或危害辨识,确定其自身活动可能发生的危害和后果,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手段和控制措施,以减少可能引起的人员伤害、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20]该理念的推广和贯彻有助于保障职工健康和实现企业人性化管理,并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
(五)推进公众参与
美国风险评估制度建立之初,受到很多学者抨击的原因之一,即是其难以实现环境正义。在评估过程中,难以有效的考虑到贫困地区居民的需求,同时评估样本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公众难以有效地参与到风险评估过程之中,都是过去曾经存在的问题。[2]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便产生了风险沟通机制,该机制旨在使可能受到潜在的环境污染所致危险的人知悉其人身、财产和所在社区受到的影响。美国学者将风险沟通定义为在高压力、高关注度或争议的情况下基于科学的有效沟通的方法。然而,从风险管理角度而言,风险沟通的目的则在于帮助受影响社区的居民理解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流程,以形成对危险物质的科学有效认知,并帮助其参与到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决策过程之中。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贯穿始终,过程公正,并且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并有能力解决所有沟通中产生的问题。理想的风险沟通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在政府机关和有关组织通知受影响居民后,再由受影响居民将他们的想法告知政府机关和组织。[21]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进行了专章规定,是我国对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愈发重视的具体表现。因此,在构架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体系中,应将公众参与贯穿于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全过程。一方面,在受影响社区居民对损害或者潜在风险有着较为合理的认知的前提下,当地政府及主管机关应积极与居民进行沟通,以实现风险管理效果的最优化。另一方面,应发挥科研机构和高校在风险评估制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及时开展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为风险评估制度的建立提供科学性和权威性保障。[22]33
五、结论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而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破坏的同时,亦对人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危险性。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广泛性,导致环境健康问题亦具有多样性,而严重的人体健康问题往往难以治疗与恢复。而有效的风险管理,则是控制环境健康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通过进行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在减少风险不确定性的同时,有助于降低环境健康问题的发生几率,保障人体健康。
完善和构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保障人体健康。并且,我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已经将保障人体健康作为法律实施目标之一。同时,我国2007年发布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2011年发布的首个“十二五”环境健康的工作规划以及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都为建立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方向性指导和基础。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充足的法律支撑,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环境健康法律法规体系,更未形成完善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
目前,我国环境资源法制体系仍以环境管理为主要目标、以城市环境为主要管制对象、以行政管制作为主要管理手段。[23]这种传统的环境资源法制体系中缺乏对人体健康的足够关注,使得保障人体健康这一重要的环境法制目标之一,至今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并且,我国亦未构建科学的环境污染人身损害鉴定法律制度,在环境污染发生后,难以有效的评估人体健康损害程度。[24]为此,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体系,对于保障人体健康和完善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5]
美国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管理,在科学技术手段与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不断磨合与融合中,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而科学的风险评估方法。并且,逐步形成集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于一体的风险评估制度,该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鉴于我国当前存在的环境健康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为全面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保障人体健康目标,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于文轩:《美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1年第3期,第57页。
[2]Robert R. Kuehna.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Implications of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J],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6, 103:2.
[3]Dennis J. Paustenbach. "A Survey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n D. J. Paustenbach, ed., The Risk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Hazards: A Textbook of Case Studies, 1989, 27:35.
[4]J. Donald Millar,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A Tool to Be Used Responsibly,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1992,13(1): 5,11.
[5]Lester B. Lave,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0, 99(3): 235,240.
[6]U.S. EPA: Risk Assessment,https://www.epa.gov/risk/about-risk-assessmen.
[7]U.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Identifying and Regulating Carcinogens,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ota/Ota_3/DATA/1987/8711.PDF,1987:199.
[8]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 1983:42.
[9]Mark Eliot Shere, The Myth of Meaningfu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19 Harv. Envtl. L. Rev. 1995:420.
[10]钟瑞华:《从绝对权利到风险管理——美国的德莱尼条款之争及其启示》,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第584页。
[11]Andrew J. Miller, 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 of 1996: Science and Law at a Crossroads, 7 Duke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Forum,1997:393.
[12]Charles F. Mills III, Global RBCA: Its Implementation, Foundation in Risk-Based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J. Land Use & Envtl. L. Vol. 22, No. 1 (FALL 2006): 102.
[13]U.S. EPA, Risk Characterization,https://www.epa.gov/risk/conducting-human-health-risk-assessment.
[14]U.S. EPA, Risk Characterization Handbook, 1(2000).
[15]于文轩:《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预防原则——从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则案例谈起》,载《中国环境法制》,2007年第1期,第244-246页。
[16]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17]吕忠梅,杨诗鸣:《控制环境与健康风险:美国环境标准制度功能借鉴》,载《中国环境健康管理》,2007年第1期,第58页。
[18]参见王曦:“中国环境治理与规则:一个概念模型”,载于文轩主编:《环境资源与能源法评论(第1辑):生态文明语境下的环境资源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1-32页。
[19]王晓晖,喻广华,高静:《中国企业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者胜任能力模型研究》,载《管理科学》,2012年6月第25卷第3期,第1页。
[20]张立勇:《浅谈企业HSE文化的培育与创建》,载《吐哈油气》,2008年第13卷第2期,第198-200页。
[21]U.S. EPA:Risk Communication,https://www.epa.gov/risk/risk-communication#self.
[22]吕忠梅,黄凯:《论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载《北洋法学评论》(第一卷),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23]马骧聪:《论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及健全环境资源立法》,《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第61-63页。
[24]孙佑海:《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如何依法有序发展?》,载《环境保护》,2016年第24期,第32页。
[25]孙佑海:《严格环境执法保障公众健康》,载《环境保护》,2017年第6期,第30页。
作者简介
孙佑海,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朱炳成,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