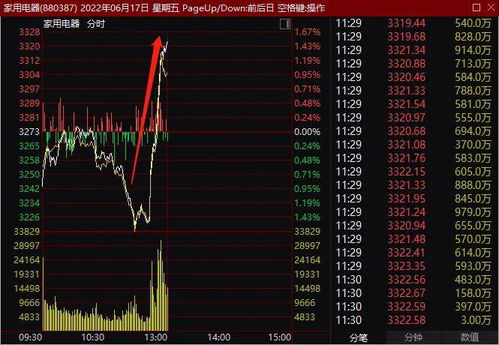(图源:国家林草局官网)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中国将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从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以来,国家公园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成为许多国家独具特色的“国家名片”和生态安全的屏障。而如今,作为国土面积大国和生物多样性大国,中国也终于拥有了第一批国家公园,并将继续建设约50个国家公园,形成国家公园体系,进而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系列建设规划将为中国的生态保护领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中国又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去科学地建设和管理国家公园?
在这次由《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编委、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研究员主持的论坛中,几位亲身参与中国国家公园研究与规划的生态保护专家齐聚一堂,对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未来规划,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并尝试提出对其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主持 ▼
_
马克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专家 ▼
_
雷光春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
欧阳志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
苏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锐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
张玉钧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
整理撰文:
赵维杰(NSR新闻编辑)
中国的国家公园,会是怎样的“公园”?
马克平:欢迎各位专家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公园是什么?它的定位是怎样的?
杨锐:“国家公园”里面有“公园”两个字,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一个为人服务,供人观赏游玩的地方。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国家公园的一小部分功能。从本质上讲,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种类型,它的首要目标是自然保护和生态保护,尤其是对大尺度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保护,同时也兼顾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社区生计等其他目标。所以说,国家公园不是旅游度假区,也不是完全禁止人类进入的自然保护禁区,而是一种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标,兼容多种功能的综合形态。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公园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变化:在原始的狩猎文明时期,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始有了自己的领地,但是整体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平衡的;直到工业文明出现以后,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土地,所以在这时,人类就有义务去保护自然。
全球最早的国家公园,1872年建立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的荒野和印第安文明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所以才有人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把那里的自然环境和印第安文明保护起来。所以,国家公园实际上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机之下,国家公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庄子曾经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阐述,人会为了使用价值而去砍伐树木、利用自然,这是“有用之用”,而那些无法被直接利用的参天大树,它们的存在本身也具有意义,是更加重要的看似“无用”但有“大用”之用。我想在国家公园中,我们就是要更多地实现这种无用之用,从而达到“人与天谐,天人共美”的美好愿景。
马克平: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园相比,我国的国家公园有什么特点呢?
杨锐:中国的国家公园很有特点。首先,它出现的时间点,也就是现在,刚好是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节点。中国政府在2002年提出生态文明,在2013年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我们会更加科学地、从更高的视角出发来建设国家公园。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国家公园的规模更大。从单个国家公园的面积来看,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的平均面积是4.6万平方公里,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达到近20万平方公里,而美国62个国家公园的平均面积还不到3400平方公里。从国家公园在国土面积中的占比来看,我们预计在未来建设50-80个国家公园,将占国土面积的8-1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3%,全球平均约为3.4%。
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建设速度很快。从2013年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到2021年10月12日,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只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其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速度尤其快,从提出设想到正式设立,只有三年的时间。
第四个特点是我们的保护力度很大,中央政府对生态保护有着非常坚定的领导意愿。当初发改委组织专家讨论,上报给中央的意见中写的是“生态保护优先”和“更严格的保护”,而中央文件下来时写的是“生态保护第一”和“最严格的保护”。习总书记更是多次将国家公园建设称之为“国之大者”,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生态保护的决心和魄力。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建设国家公园的难度也很大。中国有14亿多人口,而国家公园所在的常常是老少边穷地区,因此国家公园的建设中将面临许多难题,包括复杂的土地所属和管理权限、当地居民的人居环境改善期望、以及如何统筹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关系等等。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应该是世界上难度最高、挑战性最大的。
马克平: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是按照怎样的原则、如何挑选出来的?未来还有怎样的布局和计划?
欧阳志云:我们建设国家公园,是为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基础。因此在进行国家公园的整体布局时,我们考虑的主要标准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要具有国家代表性,具体又包括代表性的生态系统、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以及代表性的物种。在实际筛选中,我们发现这三条代表性常常是彼此重叠的,比如大熊猫生活在秦岭一带,海南的热带雨林中有长臂猿,这些地方都既有代表性的物种,也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第二点,这些地区应该对国家的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比如,三江源是亚洲水塔、中国水塔,为黄河流域提供了40%左右的水资源,对我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而海南热带雨林也具有重要的涵养水源的功能,是海南岛干旱季节的重要水源。
第三点,这些自然区域应当具有比较高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真性是指遭受人为破坏较小,还保留着比较好的自然状态。完整性是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比较完整,或能够支撑代表性的物种繁衍。这就需要我们在确定每个国家公园的范围时,需要根据保护对象的特征进行深入的调查、评估、分析与设计。
第四点,这些地区应当具有较好的自然保护管理基础,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国家公园体制,并进行有效管理。
在这样几点考虑之下,我们首先从代表性和对国家生态安全的意义出发,结合已有的全国生态地理区划、全国植被区划研究成果,从全国3800多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筛选出了200多个候选区域。然后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对完整性、原真性等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评估,从中筛选出80多个适合设立国家公园的区域。
第一批的五个国家公园,就是这80多个候选区域中保护价值高,管理运行机制相对成熟的五个。预计到2035年国家公园的数量将达到50个左右,最终可能达到80多个。当然这只是目前的估计,最终的数字可能会有变化。最重要的是,应将全国应该保护的地区保护起来,建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公园体系。
雷光春:关于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我想补充两点建议。第一是要考虑时间尺度和生态系统的演变,全球的气候正在发生改变,这将会影响物种的迁移扩散,改变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所以我们在考虑空间布局时要有长远思考,需要重视现在看来还不突出,但在未来可能十分重要的生态区域。
第二是要考虑地域的平衡。因为国家公园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要为全社会提供认识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参与自然保护的机会,所以也要考虑地域平衡,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比较方便地接触到国家公园。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马克平:我们经常说要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个体系将是怎样一个体系?为什么说国家公园是其中的主体?
雷光春:在中国正在建设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除了国家公园,还包括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最终将形成一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保护地体系,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顶层设计。
在这个体系中,之所以说国家公园是主体,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在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中,国家公园的面积占比将是最大的。第二点,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大尺度的自然保护地,可以为生态系统中复杂、动态的生物网络和生态过程提供更完整、更系统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欧阳志云:按照规划,我们将会把中国最重要的、最具国家代表性的区域都划为国家公园,所以这些国家公园当然也会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部分。
马克平:我们所说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是在实施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而除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4月18日揭牌成立的“国家植物园”就是植物迁地保护的一种形式。所以我想,我们未来是否也可以建立一个以国家植物园等为代表的“中国迁地保护体系”,并与自然保护地的就地保护体系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在我国,目前植物迁地保护的系统性要略高于动物,我们有规模庞大的植物园,还有植物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圃,也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标本馆、实验室等,可以为各种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和研究提供支持。在动物方面,迁地保护在国内外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我们通过人工繁育,将朱鹮种群从7只扩展到5000多只,在放归自然之后,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野外种群;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救护站和繁育基地,也都为这些动物的保护与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的以猎奇、观赏为主要功能的动物园,有很多保护学家认为它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形式,应该针对保护目标加强迁地保护功能。总之,我们可以考虑将这些动植物迁地保护的方式和基础设施进行统筹布局,形成一个国家级的迁地保护体系。
此外,如何将迁地保护体系与就地保护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和支撑,为每一个受威胁物种提供最有效的保护,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张玉钧: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的结合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以植物为例,一方面迁地保护对于一些非常濒危的物种非常重要,例如,北京百花山的槭叶铁线莲和百花山葡萄都已经岌岌可危,通过迁地的方法将它们收集起来进行挽救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迁地保护也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在建设植物园、将各地植物集中起来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等温线”的概念,考虑这些植物被移植到新的气候环境之后,是否能保持原有的生态型,并健康地生长。例如,油松广泛分布于华北地区,但在自然环境下,它们主要生长在海拔几百米以上的高度,因此将它们移植到低海拔的城市和植物园时,它们的生长情况常常并不理想。所以我想,未来的植物迁地保护体系中,一定不只有一个建在北京的国家植物园,也要包含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许多植物园形成的网络体系,才能全面地保护中国的各类植物。目前,我国有些植物园,比如秦岭植物园,开始尝试迁地和就地混搭的模式,一方面就地保护秦岭当地的植物,同时也引进一些外来的植物。我想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模式。
国家公园:美丽中国的最美国土
马克平:2019年中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将国家公园称为“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那么,国家公园在美丽中国建设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苏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什么是美丽中国。很多时候许多人只是提天蓝、水碧、土净,但如果只是这些,那和美丽美国、美丽法国有什么区别呢?这些是世界各国对美好人居环境的共同追求,但是并不能代表全面的生态环境,更不能体现有国家代表性的美丽。资源上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才能真正全面展现出美丽中国的独特形态。可以说,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措施,在比较容易的人居环境改善后,更应该是主要措施。这是因为人居环境破坏后容易恢复,而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不仅影响全面且一旦损失万劫不复,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才是国脉所系,所以中央文件里将其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
中央文件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而正如欧阳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在2035年将建成5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也将基本成型。到2035年,我们的国家公园体系基本成形,也就能够呈现出美丽中国的风貌,呈现出生态文明的新体制,甚至可以说,呈现出建党百年文件中所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想,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能够支撑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绿色发展,也将成为世界范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样板。杨锐:国家公园将是美丽中国中最美丽的国土。而且我认为,美丽中国不仅是自然之美,也包括人的心灵之美。国家公园除了作为自然保护用地之外,也是培养人的真善美品质的最好载体。
马克平:杨老师说得很对,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让国家公园成为公众亲近自然、培养人类美好品格的载体?
张玉钧:要思考搭建国家公园全民共享机制,打造科研基地、自然教育和自然游憩的公益性服务体系和经营性项目。国家公园的职能之一是要对公众进行自然教育。国家公园中会有一小部分对公众开放,为大家提供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机会。与此同时,也通过解说等各种方式,让大家能更科学地认识自然,参与到保护自然生态的行动中去。这需要公园管理者、科学家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据我所知,许多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都在花大力气做这件事情。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拿出一笔专项资金,和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合作,从撰写解说词,制作自然读本、鼓励自然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来推动自然教育。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应该为公众提供哪些资源、让公众了解哪些知识?首先,可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国家公园,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此外最重要的,就是结合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公园,为公众讲好“自然故事”。比如,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就可以讲松鼠和倒木的故事:在早些年,护林员看到森林中的倒木,会把它们清除出去;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松鼠常常将收集的红松种子埋藏在这些倒下的树木中,而随着树木的腐烂,这些种子就会发芽,成长为新的树木;在了解到这些规律之后,就调整了处理倒木的方式。通过这些故事,公众很容易就能理解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也了解人类保护自然的科学方法。
科学的保护
马克平:刚刚我们从几个角度讨论了国家公园和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定位、规划、价值和意义。接下来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一下,如何才能科学地做好生态保护,让国家公园真正发挥应有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规划每一个国家公园的范围,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划一条线,要每一个国家公园都达到多大的面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要保护藏羚羊,就要考虑它们的大尺度迁徙,这样一来,就需要把羌塘、阿尔金山、可可西里整个一大片地区都保护起来,整体的面积可能需要达到40万平方公里,才能体现出这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对于东部一些以常绿阔叶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不需要太大的面积,就能够完整地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
苏杨:确实,对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和不同的物种,需要不同的保护方式,不能以为保护就是一禁了之。比如,不同的动物对于人类道路的敏感性是不同的。之前欧阳老师团队的研究发现,大熊猫对道路非常敏感,它们会避开人类修建的道路。所以道路会使它们的栖息地碎片化,严重影响大熊猫的生存。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其他动物,从青藏高原的有蹄类动物到农林交错地带的多种有蹄类、食肉目动物和鸟类,它们其实对人类低等级道路的适应性很高,而且它们也和人类一样,更喜欢走这种相对平坦的道路,只是它们走的时间不同,可能会在晚上,各种动物在同样的空间有不同的生态位。所以在野外考察时经常会发现,沿着人类建设的简易道路这一条线,物种多样性反而丰富,红外相机能拍到更多的物种。而即便是较高等级的道路,像青藏公路那样,只要在动物迁徙的季节根据动物穿越公路的时间对机动车进行严格的管理,就能既有藏羚羊的正常生活也有高原车队的正常交通。所以,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的时候,更应该把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理解为“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用适应性管理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去选择个性化的、精准的方法,而不只是简单的“核心保护区禁止人类活动”。
雷光春:科学的保护还涉及很多细节。在中国,提到要进行严格的自然保护,常常会要求严格控制森林火灾、禁止农民放牧,甚至要把当地居住的老百姓都迁出去。但是这些措施其实并不符合自然规律。在自然界,森林火本就是周期性的自然现象,支撑着各类动植物的平衡发展。我知道在芬兰等很多国家,人们甚至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人为放火,来调控森林生态系统。关于放牧,英国也有过一个例子,人们为了保护一个地区的蝴蝶而禁止放牧,结果当地的植物群落发生了演替,到20年之后,当地的蝴蝶反而完全消失了。
马克平:生态移民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也还需要认真思考。我记得贵州梵净山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时候,准备的资料里特别写到,当地政府为了让保护更高效,将许多户当地居民从保护区迁出了。但是国际专家对这一点很不理解,他们认为当地居民也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应当针对保护目标适当约束他们的行为,但不应该将他们迁出去。
欧阳志云:关于放牧的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禁止放牧不是一定会改变原有的植被。因为在人类饲养的牛羊不去吃草以后,可能会有野生动物去吃草,填补这个空位,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数量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据说藏羚羊的种群已经从几万只恢复到了30万只。
马克平:对于藏羚羊已经有30万只这个说法,我一直十分怀疑。这个数字很可能并不是实际调查的结果,我认为实际上的数字不可能这么大。
雷光春:中国确实存在种群数量统计的问题。现在国内有人说,中国的鹅喉羚总数已经有20-30万只,但是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数据库中,全球的鹅喉羚总数只有4.2-4.9万只。
体制的保障
马克平:在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过程中,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苏杨:现在的核心问题,也是全世界所有自然保护地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具体来讲,目前最紧迫的就是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权利,不要将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逼到国家公园建设的对立面上去。
事实上,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从2017年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事件开始加速推进的。在祁连山事件的背景下,2017年6月26日,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设立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方案;紧接着7月27日第三十七次会议就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从那时起,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就开始对各类保护地进行比较严格的督查。但遗憾的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还只能用过时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当尺子,比照这种尺子“一刀切”式的督查在及时纠正乱象的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伤,让部分地方政府产生了“建国家公园就是要设禁区、会影响地方发展”的认识,这就会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整体推进造成巨大的阻碍。
比如,上海的崇明东滩保护区,原本保护和管理得非常不错,那里的互花米草治理工程历时十几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却说,那里建设得很好的科普基地属于高档政务接待设施,要作为反面教材来处理。后来这件事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被解释清楚了,但与此同时,长江口国家公园的创建就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要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在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的基础上,明确地方政府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责权利,让大家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至少要保证大家不会为建设国家公园出力之后,反而被追责。否则的话,要在2035年建立50个国家公园,一定是十分困难的。
而且事实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本就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要学会用科学可持续的方法,而不是过去消耗式的方法去利用大自然中丰富的生态资源。比如,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景观和物种可以带来独特的旅游体验、形成最好的自然课堂,丰富的基因资源可以为药物研发和特色农业提供许多产业机遇,这些需要新的业态来转化,这也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所说的“生态产业化”。只有让当地百姓从生态产业化中受益,才能使地方政府和基层百姓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形成共抓大保护的生命共同体,从而形成推动国家公园建设的合力。
张玉钧:如何使当地人受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东北林区,原本居住着很多林业局的职工,在向国家公园转型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成为生态管护员,一部分可以进入生态旅游行业,但是也会有很大一部分需要转向其他方向。总之,如何让当地人受益,其实还需要探索与思考。
欧阳志云:体制机制的建设要比规划国家公园布局困难得多。在参与国家公园评估过程中,我们发现管理机构的整合就是一个难题。在将现有的自然保护区、各类公园等保护地整合成国家公园的过程中,要对这些保护地管理机构进行整合,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需要整合几十个保护地管理机构,这涉及到许多员工的转岗与安置问题,难度非常大。尤其是对于跨省级行政区的国家公园,困难更多。
此外,我们还没有明确国家公园应当怎样建设,在国家公园里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导致各个国家公园都在观望。所以我们需要尽快完成《国家公园法》的立法,让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让实施者知道应该如何划分国家公园内的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在不同的区域内是否可以进行资源利用、自然教育和旅游活动,能够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当地百姓的生活应当如何安排,他们的生产活动方式需要哪些改变,等等。只有让这些具体的事项都有规章制度可依,国家公园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并健康发展。
三种类型的“国家公园研究院”
马克平:在过去几年,国内成立了不少“国家公园研究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各个国家公园自己成立的研究院;一类是由主管部门成立的研究院,比如欧阳老师所在的由国家林草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的研究院;另一类是由高校等独立科研机构成立的研究院,比如杨锐老师所在的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这些研究院各自的侧重点分别是什么?将为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起到怎样的作用?
雷光春:各个国家公园自己成立的研究院,我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建成一个开放的研究平台。一方面它可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针对自身需求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为从事相关研究的更多团队提供资源和平台,促进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进步。
欧阳志云:由国家林草局和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共同建立的国家公园研究院,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研究平台,和大家一起去开展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研究,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解决方法和科学依据,以及政策建议。我们既要研究共性的问题,也要研究各个国家公园的具体问题。其中共性问题包括基础性科学问题、管理政策问题、管理技术问题等方面,比如,如何评价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每个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责任与管理权限,如何合理布设红外相机,在不干扰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管理。而非共性问题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海南的长臂猿在什么样的树冠中生活得最好,栖息地如何恢复,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的道路应该如何规划,等等。总之,我们希望各个国家公园和所有的研究者一起来提出问题,再一起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杨锐:作为一个高校研究院,清华的国家公园研究院会侧重于去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整体性的,以及面向长期未来的前瞻性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国家公园的思想基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规律的研究,也包括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去研究自然保护地的“气候避难所”,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布局优化和长期规划提供支撑。
我想国家公园研究院是可以多一些的,就像生态系统需要物种的多样性,研究机构也需要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研究院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最终才能形成合力,为中国国家公园的未来发展,以及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平: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我们今天一起讨论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定位、特点、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也对如何科学地设计、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思路。我想,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各领域的专家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文是《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Forum文章“Beginning: China's national parks
system”的中文版本,英文原文:https://doi.org/10.1093/nsr/nwac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