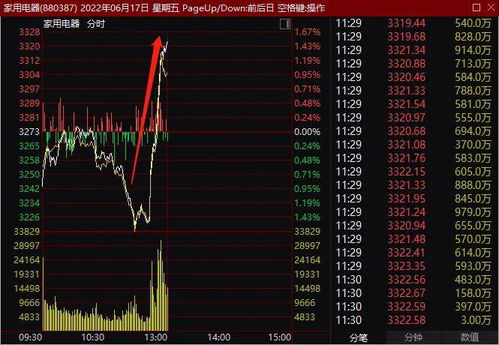人类学家项飙说,当代人的生活,“附近”逐渐消失了,我们依赖各种无形的系统与外界连接,通过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之中,对转瞬即逝的热点了如指掌,精力和兴趣在不断消耗。与此同时,对居所周边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环境的细节和运行机制,以及更深远的历史和记忆,则缺乏描述的能力和探索的兴趣。人们仿佛处在被格式化的同质空间之中。具体而言,不少人们处于“吃饭点外卖,出门打滴滴,进出电梯看手机”的状态,通过移动互联网,对所谓网络热点了如指掌。这也许是导致人们在享受空前便利舒适的同时觉得精神压抑和空虚的一个原因。项飙指出,现在的城市空间功能性过强,但“生态性”不足,系统通过计算,介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些无用的、自发的东西不见了。人们算计着的同时被算计着,如何重建生活的后方,也许可以从探索“附近”开始,具体而言,居所周围的“最初500米”,成为我们认识附近,重建丰富日常生活的大后方起点。当然,这种探索首先面临的是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界限。
2022年春天,我搬到双流机场附近的成都市区西南部边缘。新开通地铁线路终点站附近,一切崭新。小区门楼的石材贴面上几何形态的立体凸起和具有几何线条的灯具以及围栏上金属制成的卷曲植物图案掺杂着Art-Deco(装饰艺术)和Art-Nouveau(新艺术运动)风格的符号,古典复兴的三角形山花和门楼下比例不那么协调的罗马柱式杂糅在一起,设计小区的建筑师似乎在暗示自己不甘于被毫无挑战性的商品房住宅小区项目束缚灵感和发挥的空间,向他或她的业主彰显自己的建筑修养以及小区并不平庸的品质——当然,我很怀疑有多少小区的住户注意到建筑师的用心,人们在选择住房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在有限的预算中尽可能挑选合适的楼层和面积,无暇他顾。不过,拼贴与杂糅,是中国郊区景观的普遍形态:符号与符号叠加,意义变得模糊,建筑和空间本身如同广告牌,嵌入不同的空间肌理之中。
周边的地块呈现出不同面貌:有春天开满油菜花、冬天衰草连天的农地;有大型仓储物流中心:庞大到横贯整个街区,不时有大货车出入其间,轮胎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巨大的噪音,如同巨兽呼啸;有近二十年来新建的各种类型的小区,大同小异,有着稀疏的底商、封闭的围墙内依照不同的规格配置的园林植物和运动设施;也有农村拆迁安置小区,房屋紧凑,缺乏绿地和公共空间,低层多为临街的门面,餐饮业主将桌椅摆在了门前的公共空间,食客在品尝火锅、冒菜和烧烤时,与跳广场舞的阿姨并行不悖。秩序稍显混乱的同时,空间充满了不羁的烟火气。
时间维度的遥远与物理空间的阻隔,成为我们理解附近的障碍。在水平方向上,空间存在许多阻隔,不同形态的墙,挡住人们的脚步甚至视线。只有当人们采取鸟类的视角时,空间肌理才能袒露其秘密。然而,迈开脚步带上好奇心开始探索,就像打开书卷一样,总会有所收获。就在我所居住小区的东南方向直线距离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始建于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址,进入其中,像是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界面,它离我如此之近,从我家阳台俯瞰,能清晰地看到那些灰暗陈旧的厂房屋顶一成不变,而周遭繁茂的植物从春到冬,不断转换颜色。于是,我开始进入这个近乎废墟的工业遗址,进行“考现学”式的探索,辅以相关资料的查阅,最终有了这样一篇笔记。
这座工业废墟,是前四川齿轮厂所在地,现在的地图上将其家属区标注为“莲花社区”而未写明“四川齿轮厂”。四川齿轮厂是“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的工厂之一,资料显示:“1964年底,八机部为贯彻‘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的方针,决定天津内燃机齿轮厂内迁,当时,天津内燃机齿轮厂的部分干部职工及家属200多人不远千里,奔赴大西南。带着设备来到牧马山,与原成都拖拉机厂的干部职工一同组建了四川齿轮厂。”[ 文字来自莲花社区“川齿记忆”宣传栏。]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线建设的企业还经历过一个调整时期,原本位于成都远郊郫县山中的岷江齿轮厂于1983年迁出并入四川齿轮厂。此后的一段时间,川齿厂进入鼎盛时期,引入新的生产线,员工多达两千余人,年产各类齿轮配件上百万件。这段短暂的辉煌大概持续到了九十年代初,此后便是漫长的衰落,直到2005年,川齿宣告清算破产。厂房和办公区域开始了废墟化的过程,家属区则重组为莲花社区。
如今,老旧楼宇上的“川齿”两个大字也显得颇为陈旧。
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周边的地块以不同的速率演变,有些缓慢,有些迅速,有些则近乎停滞。在形成当下景观之前,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景观和空间肌理的变化背后,是数十年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不同的人群在空间中来来往往,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时过境迁之后不为人所知。建筑史学者黄全乐曾经指出,1949年之后,五十到八十年代之间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和农村都是国家这台大机器的组成构件,受到国家的统一、直接的领导和组织。建国以来逐步建立和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把它们各自‘格式化’,彼此分开,并在城市与农村实施不同的土地制度和福利系统。”这一基本社会经济机制决定了可见的空间肌理与城乡景观,城乡接合部的物理空间在视觉上常常呈现出看似无序的状态,但其背后仍隐然有着具体制度之下的运转逻辑:“当时,城市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征用近郊的农村集体用地,以把新建设的单位安插到农村土地上去的方式,是一种点状的、嵌入式的城市扩展。由于那个时代全国性的总体资源匮乏,城市没有能力完善整体的、覆盖所征收的村庄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跟进建设。更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缺位,城市的零星扩张始终缺乏规划的制定和指引,城市单位的征地充满了随意性且彼此互不相关,因此导致了郊区土地变得越来越破碎、零散。”正因为如此,当最近二十多年城市大规模向郊区扩张之前,这些乡村与城市的交界地带所分布的各种属于城市的单位,就以不规则的形态分布在田野之中:“位于‘农村世界’范围内建造、却隶属于城市系统的单位社区们,并没有与其邻近的郊区村庄建立积极而有效率的空间连接。一个个属于城市体制的‘单位’就像由围墙围住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如孤岛般漂浮在农村广阔的耕地载体上。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空间无规划的‘产物’,这些零散的土地将成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改造的底板和基地。”如果对照早些年的卫星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川齿厂和周边地块的形态,如同孤岛的单位院落星散在不规则分布的农田和聚落之中。
在数十年前,四川齿轮厂是这个片区最早“城市化”的地块,四周都是农田。如今,城市的前线已经到了几百米开外的地带,废墟隔着一片已经有挖掘机施工的荒地与远处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对垒。城乡之间的空间拼贴,同时也是不同时段的拼贴。
2024年3月,川齿厂对面的空地,油菜花盛放,越过绿色围挡的高度。这个地块是今天周边不多的尚未建设的区域。
自上而下的规划力量缺位,非正规的力量开始进入空间。建筑和空间的意义都随之置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废墟是一个脱离了原有功能,随着时间演变并被不同力量重新定义的非正规空间。
对比2001年和2023年的卫星地图,可以明显地看出:之前的农田和农村聚落消失了,被各种楼盘和安置小区以及新建的仓库厂房所取代。与周边沧海桑田式的变化相比,川齿厂本身则变化缓慢,成为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固定坐标。如果说在数十年前,川齿厂的厂房与院落如同城市嵌入农村的孤岛,那么今天,川齿厂则成为了时间的孤岛。黄乐全的论断主要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州,但事实上,作为内陆省会的成都在城市形态和演变的过程中,也基本类似,只是城市扩张的时间节点更晚。当城市狂飙猛进,房地产作为先锋把城市的边界拓展到以前的城乡接合部的时候,原来的孤岛则逐渐随着国企改制、破产等一系列变迁而逐渐沦为废墟,逐渐凋零、老化,或者被赋予新的用途。如同潘然在《废墟美国》中指出废墟中建筑物的未来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扔在原地无人问津地闲置,也就是最常见的废弃(abandoned);第二类是拆除(demolish);第三类是修复或翻新(restore or renovate),而第三类也常常包含另一小类:另作他用(repurpose)。”川齿厂的厂房,第二和第三种情形都有,并且因为不同的用途,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面貌。
废墟是时间的飞地,那里的一切处在与外界不同的时间速率之中:衰败、腐烂、转化、新生。正如艺术史家巫鸿所言,许多当代废墟“在现场空置多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正常生活之外。‘时间’似乎在这些黑洞里消失了,它们的过去被销毁,它们的未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谜”。
晴天的黄昏与午后,光线在建筑物与植物之间雕刻变幻的阴影,刚硬或者柔和的线条不断移动,四下静谧,偶有风拂过叶子的声响,营造出一种适合怀旧的氛围。我在前后两年之中的不同季节进入川齿厂的旧址,看到随着时间推移和季节变换,废墟本身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是周期性的,有些则不是。周期性的变化与自然物候和废墟之中的农业生产有关,非周期性的变化则大多是新迁入的人群和机构对建成环境进行的改造,有时很微小,有时则较为剧烈,但与很多被纳入城市更新项目的工业遗址不同,自上而下的整体性规划和设计始终是不在场的。
从川齿厂的北门进入,首先是一条南北向的陈旧水泥路,左侧的厂房在2023年春天已经是物流仓库,但门框两侧仍有斑驳的旧日标语,提示这个建筑的建成年代。
2023年4月,厂房门两边的标语油漆已经斑驳,大致能看到“永远跟着毛主席……”
继续向南前行,位于右手边也就是西南方向,可以看见整个川齿厂区的地标性建筑——建成于1991年的科技计量楼(事实上更多有办公楼和会议室的功能,详见后文)。在其前方,原本的绿化带已经被人种上农作物,春天是油菜,在收获油菜籽之后接着种植玉米。
我曾经在夏天玉米秧苗种植不久之后发现正在耕种的两名老年男女,2022年夏天的时候,他们将川齿厂院落之中所有未被硬化的土质地面开垦为农地。农业侵入了曾经属于工业的领地,在外部,城市已经在五百米外建立了高耸的桥头堡,而在工业废墟的内部,农村收复了失地,在曾经属于观赏植物的绿化带种植了玉米、油菜、蔬菜。我脑海中冒出“黍离麦秀”这个词,曾经在国有企业大院生活过的人们,看到眼前此种景象,唤起的情绪与旧时遗民当有相通之处。
2024年3月,又一个春天,油菜花盛放,但此楼已经被改为物流仓库,写着“闲人免进”
2023年4月,油菜籽已经成熟,等待收割
2022年6月,油菜收割之后,原有地块种植了玉米
2022年6月,正在另一片玉米地耕作的两名老年男女
2022年6月,一间仓库前已经一人多高的玉米
高达六层的科技计量楼,外立面贴着九十年代初流行的长方形瓷砖,窗框则是当时颇为时髦的铝合金平推窗,配上茶色玻璃,在建成之日可算气派。
我在一个春末的黄昏进入楼中,有些场景凝固在遥远的过去,有些则因为后来的临时访客或者住民,在废墟中留下了新的痕迹和信息。
一、二楼的许多房间有人进入并长期居住,也许就是种植农作物的老年男女,因为在空旷的办公室中,堆放了收割之后的粮食,据称是“要去制作饲料喂鸡”的。
2023年4月,二楼办公室中堆放的粮食所制成的饲料,据说是要“用来喂鸡”,如同某种装置艺术。
布满废弃物的二楼走道能看到地面上有些可能是曾经的住户留下的被褥等物。
有些房间后来搭建的木质门板上写着:“此房已住2人,请勿破门,回家”
一间办公室的门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下部写着三个红色大字“请勿开!”
放置了两张竹木单人床的房间,床头有草席和较为新的矿泉水瓶。
某层楼的小会议室,门框玻璃已经破碎,地面上的杂物中有疑似被褥枕头等。
新住户们比较乐于挑选低楼层两端采光较好的房间居住,二层以上的房间大多没有人居住,可以看到零散的属于川齿厂的遗存,包括家具和物件,它们停留在九十年代初。另外,高楼层未见到后来进入者长期居住的痕迹,但仍可见不少之前访客或者短暂居住过的人们留下的涂鸦和生活用品。我在四楼会议室的地上看到一本四川齿轮厂《炉排变速器维修手册》,这是工厂尚在运作时代的孑遗之物,封底上印着当年的厂址:四川成都市南郊;五位数字的电话号码:52871/52872;电传(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的通信技术):60170。
布满灰尘的四川齿轮厂《炉排变速器维修手册》,被遗弃在一间办公室的地面上。
《炉排变速器维修手册》封底,写着当时四川齿轮厂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脱落的封底上附有“四川齿轮厂技术图书室借阅卡”
在西侧的外设楼梯上,我看到印着北京字样的老式旅行包。
老式“北京”旅行包
头盔:在空旷的办公室中央,有一个不知何人在何时留下的黄色头盔,也许来自外卖骑手,应该是骑摩托车或者电动车时使用的,但现在被弃置于此。
被弃置的外卖骑手头盔
楼梯间的老式灯具
办公楼四楼的会议室的一面墙上,闯入者题写了各种涂鸦。“随时静录古今事,尽日放怀无间——康有为”、“心若移动、情已欠费”、“松以静延年,竹因虚收益,丁丑年 王维海”、“一帆风顺——己丑年 王维”。古代和近代的文化名人,也许对于涂鸦者而言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本”,尽管诗句和对联的作者都并非涂鸦者所标注的。他们或她们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过这些名字,便随意将其标注在墙上。爱情与理想,是这些涂鸦的主题。
墙面涂鸦之一
墙面涂鸦之二
或许可以挪用鲁道夫斯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概念,将这些涂鸦和物件堆砌称之为“没有艺术家的艺术”,这些作品的作者随性地在废墟中创作,各有目的,但并未为了艺术。
继续向上攀爬,高光时刻随之来临,夕阳西下,我在六楼西头空荡荡的大会议室中,遭遇以下画面:
“鹏程万里”:一幅九十年代风格的装饰画右上角的四个字标明画作的主题,画的近景是两棵相对的迎客松,远景则是松树背后云雾缭绕的山间以及若隐若现的峰峦,仿佛提示我们,前途未卜。此刻,千层板材质的画框已经破裂,向外翻转脱落,打破了画的意境。褪色的画面与残破的画框,仿佛对“鹏程万里”这个主题的反讽。五点半的阳光从残破的门框斜射入室内,被残存的窗帘随风裁剪之后,落在布满灰尘和各种垃圾的地面上,形成各种形态的光影组合。我小心翼翼地穿行其间,仿佛进入一个时空胶囊,直抵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切像是在仓促撤退之后的场景,人群消散、物件衰落、破败,灰尘堆积,但阳光和风没有变,让这个空间仍有些光影变化:好像昨天刚开过职工大会,人群各自回家。
许多怀旧的抒情性文字和影像中充满了时代错置,譬如把九十年代的生活场景当作八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段。我有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家属区的成长经历,也对当代中国建筑和不同时期的装修和家具风格有着基本的认知。所以当我在其中穿行时,断定这栋办公楼的兴建年代不会早于八十年代末。果然,在一楼的外墙上,我发现了标明建筑年代的铭牌。这栋六层楼的办公建筑,竣工于1991年7月,那是众多国企在改革开放中再次短暂辉煌时代的末尾(参见伊险峰《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描述)。至少在1992年,川齿厂仍然红火,网上能查到这一年举行共青团四川齿轮厂第九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画面中的青年工人穿着时尚,意气风发。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事实上,国企改制的步伐已经悄然而至,数年之后巨大的变化涉及无数家庭。
下午五点半的阳光穿过西面的门窗照射在地板上,风拂动老旧的窗帘,光影变化
斑驳的“鹏程万里”,是九十年代装饰画的一个常见题材。2024年初,香港M+博物馆中的一件现代艺术展品就是将多件相同题材的装饰画并置,呈现一种奇特的美学效果。
四楼会议室的西侧,九十年代风格的装修已经残破
有着九十年代风格装潢的办公室
1991年的竣工铭牌
走廊之上,九十年代风格的顶灯
我童年时代和父母曾经生活的厂区,也有建于这个时期的办公楼和车间,只是很幸运地免于了沦为废墟的命运,被更新为建立在工业遗址基础上的商业综合体。我曾经无数次在放学之后行走在类似的工业建筑之中,那个时候它们簇新、铺满时髦的马赛克,在城市的郊区鹤立鸡群。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植物的生命周期,以及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周期,单位的兴衰周期,与每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之间往往并不同步。
当代中国的废墟之中,工业废墟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它们与晚近的记忆相连,但还没有完全被“历史”收编,与那些古建筑和村镇废墟不同。巫鸿认为如张小涛的动画片《迷雾》等对重工业基地废墟的记录体现出一种“史诗性”:“这些图像从来不是私密性的或个人性的。相反,它们用来震撼观众的是这些荒凉工业区的庞然无序:有如原始怪兽一般的巨大车间,冷却了的高耸的烟囱,熄了火的炼钢炉,生锈的冷处理系统……”
“和城市废墟一样,工业废墟也不是当代艺术里的新题材。在世界各地,这类使用大量劳力、耗费巨量资源的重工业系统都处于面临淘汰的境地,它们所留下的是巨大如恐龙骨骼般的发锈钢架。”这些工业废墟不少属于“三线工程”,位于西部的偏远省份,都曾经是“经济的骄傲”。不过,巫鸿所没有谈到的是,这些工业废墟在其运转的时代,仍有其社区性的日常生活。只是不同于北京、上海那些旧城区的居民,这些工业移民社区的生活更具集体性。
“当代中国对工业废墟的表现多是对……往昔的回眸,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视角。”“巨型工业废墟和城市废墟之间还有一种区别:如果说被拆毁的民居隔日就会无影无踪,工业废墟却不会如此轻易消失。虽然已经大部分停工或废弃,它们仍具有宏大而慑人的体量。”确实如此,因为空间体量的巨大,工业遗址在成为废墟之后,仍然会在相对完整的状态之下演变,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介入,但这些介入通常不是毁灭性的。
“这种工业基地的‘死亡’从不是突然的,而只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也有可能被逆转:废弃的厂房可以因为新的目的而被重新注入生命。这里,我们发现当代艺术家对待废墟的最后一个不同态度:面对着传统民居的消失,它们的反应往往是惆怅、内省和无助。但是当面对工业废墟时,一些艺术家则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争取把它们转变成新型的艺术空间。”
“死亡”的速率和形态不同,新生的方式也各异。与著名的北京798园区和近年来遍布全国各地的工业遗址更新项目不同,川齿厂的厂房并未被更新成为艺术展览空间或是商业空间。来历不同的人群重新进驻了这里,厂区成为了农田、电动车展场、二手家具销售点、废旧家电的回收点以及物流仓库、篮球场,甚至是流浪汉的临时居所(墙上的涂鸦说明闯入者甚至利用这里即兴创作)。这些新的痕迹如同当代艺术品一样,层累地构成了这个工业废墟的时间地层,意义各不相同,众声喧哗,纷乱但充满另类的生机。这里与围墙之外的规整小区截然不同,甚至也已经与一墙之隔的原川齿厂家属社区完成了切割。在后者的一个防空洞中,布置了一个“川齿记忆”的空间,名为记忆,恰恰是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所说的“历史”,背后承载的是由官方文件、学校教科书、宣传纪律片所组成的宏大叙事。
俄裔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关于怀旧的研究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怀旧: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前者“唤起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后者则“更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并且,反思型怀旧“意识到了同一与相似之间的沟壑;家园呈废墟状态,或者,相反,经过了修葺,美化得面目全非。这样的陌生化和距离感驱使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怀旧与情感,也对应了两种类型的对废墟的态度。修复型怀旧与“时间的国家化”相连,在川齿厂的案例中,体现在与废墟一墙之隔的“川齿记忆馆”之中,在那里,残破的建筑被修复、老旧照片被重新冲洗、原本用于生产的机器被打磨得簇新,用于展示。修复意味着集体性返回原点,意味着激昂而非感伤。原本的防空洞被打造成一个“时光隧道”,在这个关于怀旧的隧洞之中,记忆所连接的是集体的高光时刻。
“川齿记忆”路牌
“川齿记忆馆”介绍牌匾
在“川齿记忆馆”外展示的机器
但是,大多数被城市更新改造过的工业遗址,经历了“士绅化”(gentrification)之后,场地原有的记忆和精神象征被掏空,麇集的创作者也承受不了高昂的租金而逃离。整个区域变得光鲜、精致,但无趣,成为商业利益链条上的一个新的打卡地点。同样在成都,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曾经聚焦从东北沈阳迁来成都,制造飞机发动机的420厂从建设到被拆迁的过程。位于成都东郊的420厂被拆迁之后,原有地块成为簇新的房地产楼盘,并取“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之句,给楼盘命名为“二十四城”,三线建设和420厂的记忆被遮蔽,诗意的名称悬浮在重工业遗址的记忆之场之上。
川齿厂没有经历这些。它的新住民以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进行“创作”。在川齿厂区,除去地标性的办公楼,其他厂房和车间大多也被挪作他用,但并未经过系统更新。
种植的农作物和自然生长的草本植物和灌木一起,侵占了原本经过硬化的土地,这似乎是一种“去工业”化,甚至“逆工业化”,因为取代工业生产的是农业,而非商业。动植物重新占领工业用地。
另外,即使那些跟“商业”有关的活动,也跟这个空间一样,与老旧和边缘相关,并不光鲜靓丽,无法在城市核心区域以及被“士绅化”的地段生存。废旧的显像管电视和空调外机像城墙砖一样被堆叠在颓败的仓库里,等待被拆卸转手。堆叠的方式既随意又有自身的逻辑,如同装置艺术一般。
有意思的是,这些电视和空调流行于中国家庭的年代,要晚于川齿厂辉煌的年代,但与厂房一样,成为了老旧之物,被抛离了时代。
二十世纪的建筑史家鲁道夫斯基提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概念,指涉那些乡村中的风土建筑,自发的营造。成为废墟的川齿厂区之中,原有的,经过建筑师设计的办公建筑和厂房内部功能和意义被转换。此外,那些“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也开始在空间中被建造。一座由空心红砖垒砌的公共厕所,通过将空心砖不同排列组合,将有空洞的一面朝向立面的手法,营造出一种本土低技派的美感。在公厕之前,由红砖垒砌的椭圆形花坛,也颇具匠心。然而很可能因为建造者不具有足够的建筑学知识,整个公厕只是有外墙“一层皮”,而缺乏内在支撑墙体和屋顶的结构,所以现状是已经部分垮塌,成为新的废墟,似乎适合放在当代艺术展览之中作为一件不俗的展品。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破败的红砖公厕
2024年3月,被拆卸的废旧汽车与油菜花地
另有几间巨大的厂房,被用于仓储、废旧电器回收:老式电视垒成的墙,如同现代装置艺术作品。猫穿行于废旧空调之间。当空间成为废墟之后,原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化,在物理层面隐喻了社会层面所处的边缘位置。
2023年4月回收的老式显像管电视垒成的电视墙
2024年3月,废品回收的业务变得更繁荣,堆叠的显示器墙放到了仓库之外。
2023年4月,回收的空调外机箱与穿行其间的猫。
成为废墟的正规建筑、废弃的非正规建筑(有艺术性的厕所,墙面有巧思,但建筑无结构),非正规建筑的坍塌,似乎是一个隐喻,重建的生活秩序并不稳定,当自上而下的力量在局部退却时,被遗弃在边缘的人群缺乏重构。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看来,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档案”,因为建筑体现或是蕴含社会关系和观念。
废墟本身仍然在自身的脉络中演变,其功能也不断被置换,推动变化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层面。
2023年4月原齿轮厂厂区的空白标识物
2023年9月,“活力篮球公园”海报,这个篮球公园利用了原齿轮厂车间。
2022年6月,外墙布满植物的废弃厂房,内部摆放了不少废弃的共享自行车。
2023年4月,正在被改造中的厂房。
2023年4月。正在被改造的厂房,原本的废弃共享单车已经被清理。
2023年4月。正在被改造的厂房,原本的废弃共享单车已经被清理。
2024年3月,之前停满废弃共享单车,一年前在施工的厂房,成为了“春天食品”的货物仓库,物流繁忙。
2024年3月,被刷成马卡龙色的仓库大门,人们将废墟改造成符合自身审美品位的样子,这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微更新。
参考文献:
黄全乐:《乡城:类型—形态学视野下的广州石牌空间史(1978-2008)》,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潘然:《废墟美国:北美铁锈地带行思录》,广东旅游出版社,2020年。
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伊险峰、杨缨:《张医生与王医生》,文汇出版社,2021年。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译林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