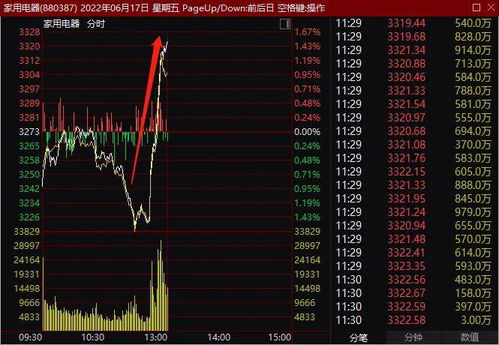在我思想逐渐成长之时,美国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在时代发展之中一步步校准了对美国的认知。起初,社会大潮不加区别地主张学习美国,此后经历了一些波澜,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布“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才定下一个稳健的基调。1994年我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师从丁则民先生学习美国西部史和移民史,完成了《二十世纪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演变》博士论文。回头看,东北师大那几年读博期间,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应该说收获巨大。
在左右振荡之中,我对美国和西方的认识就比较平衡了,既不是一味地顶礼膜拜,也不是狭隘地反对美国,而是能够比较平衡地看待美国,真正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澎湃新闻:您认为美国史专业对您日后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有什么启发?
袁鹏:当时选择美国史研究,就是想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怎么从一个只有十三个州的殖民地,一步步演变成两洋国家,进而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我们那一代学习美国史最质朴的动力。后来再研究美国的历史,就是研究其称霸世界到底采取了哪些战略和手段,这也是我们应对美国挤压中国必须学习的内容。学习美国史,对我研究国际关系帮助巨大。因为在我读书的时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还在初创阶段,正处于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地引入中国的过程,而历史学科已经较为成熟。历史学科既有中国自身从司马迁开始的上千年的学术传统,也有在苏联影响下建设起来的独立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还有一代又一代学者默默耕耘建立起的学术梯队。所以,历史学科对于弥补当时国际关系学科的苍白和机械,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国别史基础对于研究对象国的当代问题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在研究中将历史与现实的美国无缝对接。更重要的是,观察问题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这是历史学的比较优势。同时,能够基于美国的国情去看待其对外政策,这一点很重要,它能防止观点忽左忽右。
福建偷渡客与三峡辩论:与美国的初相遇
澎湃新闻:90 年代末您到访大西洋理事会,还记得第一次到美国的情景吗?
袁鹏:从1984年开始对美国研究有点兴趣,1988年读硕士,到1999年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我有一种新鲜与熟悉相混杂的奇妙感觉。新鲜感在于,毕竟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度,那时候的中美力量对比与社会发展状态反差巨大。然而,美国的种种情形都在书本上读到过,似曾相识,并不陌生。
澎湃新闻:在这期间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与美国普通人打交道的经历?
袁鹏: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当时的房东,他是从福建来美的偷渡客。一路上披荆斩棘,在海上漂了两个月,靠岸墨西哥,再入境美国当非法移民。十年后他站稳脚跟,把老婆孩子接到美国。他们这一代移民,在中国发展还不充分的时候,为了追求更优越的生活,不惜冒着妻离子散的风险,一个人孤独在美打拼,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今天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逐渐抹平了两国之间普通百姓生活条件的差异。这段记忆也映衬出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9年5月10日,中国示威者手持标语牌游行至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抗议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视觉中国 资料
澎湃新闻:1999 年5 月发生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您当时在美国期间是否与美方的专家就此进行过辩论?
袁鹏:我当时访美的时候炸馆事件已过去了半年,情况还是比较平和的。中美关系跟中日关系不一样,双方并没有累积深重的历史积怨与仇恨。也就是说中国人可能讨厌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作为两个民族而言,反而两国民间有一种相互学习,欣赏对方的历史文化的情结,这是中美关系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纽带。
澎湃新闻:在与美国专家交往中,遇到双方认知不一致的情形是怎么解决的,是否通过说理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观点?
袁鹏:改变美国人的观点是比较困难的。美国人比较强势,而且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霸权思维,但并不等于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没法沟通。比如说,在日本军国主义等历史问题上,美国的理解当然没有中国这么深刻,也无法对中国的历史记忆感同身受。由于美日之间的特殊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对日本半个多世纪的掌控,他们不认为日本是一个威胁或潜在的威胁。而中国对于日本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忧虑,显然是美国学者无法理解的。但经过不断就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日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还有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等与美国学者进行交流,应该说增进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至少纠正了他们一些比较片面的认知。
当然,最起作用的是促进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我记得当时讨论最多的就是三峡工程。美方认为修建三峡大坝,导致中国大量人民搬迁,毁坏了当地的生态和自然环境,是一个灾难。我的老家就在三峡那一带,许多亲戚仍然居住在当地。切身经历告诉我,三峡工程一夜之间改变了上百万人的命运,让他们第一次走出山沟,走进城市,得以接触外面的世界。有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乡土观念强烈,不愿意搬迁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大量的青壮年是向往外面的世界的。所以至少在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方面,三峡工程意义深远。通过我的现身说法,改变了一些美国学者的看法。
另外,美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也给我很大启发。在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我学会了要研究一个问题,先要把概念界定清楚,比如“台独”与“台湾认同”的区别。否则,前提不明确,就容易大而化之。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些年来美国专家学者对华观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袁鹏:当年美国对中国的观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正在投向西方的怀抱,认为美国在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过程中,可以改变中国甚至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体制与美国相像的国家。这是有点一厢情愿的幻想。
中国在积极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还是尽力保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也就是郑必坚先生所说的,是一条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而这方面,我想当时的美国人估计不足。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越来越有制度自信。就这个角度而言,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可能感到某种程度的失落,一些原本对华有偏见的人士,就从失落转变为幻灭,进而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把中国当作对手,强调对中国的打压。
预防、塑造、准备:做好中美关系的危机管控
澎湃新闻:过去四十年中美之间经历了许多危机时刻,而中美两国基本上妥善管控了危机,其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
袁鹏:中美关系的发展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中美关系的四十年发展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同步的。《中美建交公报》于1978年12月16日签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是在1978年12月18日,两者就相差两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功,中美关系实际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深度捆绑,互相依赖。第二个经验就是做好危机管控,我们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问题,不因为个别事件丧失信心。因此,在出现危机的第一时间就进行积极管控,不让个别危机事件冲击双边关系基本面。所以,虽然过去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类似“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炸馆事件等烈性事件,但由于我们具备处理烈性事件的意识和能力,最后总能够化险为夷,没有影响中美关系向前的主航道和主旋律。另外,注重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注重机制建设,重视民间交流,等等,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以及对华战略愈发趋向强硬?
袁鹏:根本原因还是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环顾天下,发现能令其安身立命的三要素——科技、金融、军事这三方面全方位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屈指可数,而中国位列其一。并且中国的制度越来越完备,文化自信越来越坚定,这一切都增强了美国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所以这一次美国围绕对华政策进行辩论,得出的观点较为一致,中国确实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主要对手。
第二,美国传统的接触战略以融入、改变中国的方式走不通,那么就要进行调整。调整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打压中国,而在中美利益深度交织的情况下,打压中国难度很大;第二是接受中国,然而这样又心有不甘。因此就在打压和接受之间徘徊,所以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对华新战略,在已有的对付战略对手的工具箱里面,还未找到得心应手的工具。因为中国这个对手是一个全新的对手,也是一个综合全面的对手,同时又是一个跟美国利益深度捆绑的对手,还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之路的对手。这样一个对手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对于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性现象,美国全体战略界陷入集体辩论和思考,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一个一致的答案。因此,当前处理中美关系,基本上是议题导向的,就是根据不同的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
澎湃新闻:有的美国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尚缺乏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对华战略,您如何看待这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国该如何应对?
袁鹏:现在美国之所以还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对华战略,首要原因在于受长久以来的霸权思维所困,不肯放下身段迎接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放下身段,中美双方共同构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就能实现互利共赢。然而美国经济居世界第一已有一百多年,享有五十多年的霸权和二十多年的超级大国地位,决定了它一时半会难以放下身段,反而以一个比较狭隘的视角看待其他国家的崛起。
其次,美国国内正在分裂,两党恶斗、朝野对抗,难以形成一致的战略和行动纲领。再加上从技术层面看,美国现在缺乏类似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有着世界眼光、历史记忆和深厚学养的一批大战略家去思考框架性问题。战略界往往充斥着一些政客和有一定知识,但又缺乏深厚涵养的一批人。这样就导致美国战略界思想稍显苍白,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接受其他国家的积极意见,比如习主席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他们往往从狭隘的立场出发,将一个战略性的举措视为战术性的骗局,而不是从大战略方面去思考其中的积极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局势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中国并不是毫无办法,一方面我们累积实力,让美国真实面对这么一个打不垮的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还是有相当一批人士,能够理性看待两国之间的关系,看清两国之间的利益纽带。当然,最根本一点,我们也应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我用了三个词,预防、塑造、准备:预防任何危机冲撞两国整体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塑造中美关系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准备好一旦中美关系塑造失败,能够抵御系统性风险和局部军事对抗。
2017年6月,袁鹏(左一)和“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右二)一同出席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
大变局与新秩序:以战略思考引领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实际上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对中美关系的框架设想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您如何看待2008 年美国学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提出的G2(两国集团)概念?
袁鹏:G2的想法有积极性,但提出的时机过于超前。当时中国的国力与发展势头与今日尚有差距,以中国当年的力量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说服美国国内广泛接受这一提议难度较大。再加上这还是基于大国共治的想法,不符合多极化的潮流和中国倡导的多极化的外交理念,世界大事不能由中美说了算。G2积极的一面,是愿意接纳中国的崛起。然而,这并未成为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的共识,所以非常可惜,在当年没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时过境迁,我们今天觉得这里面蕴含着积极因素的时候,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对手。在今天这个背景下,G2这一提法还是能为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启发。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对指导今天的现实有些不够用了,您如何看待美国某些专家提出的签订第四个中美联合公报的观点?
袁鹏:我的原意是:三个联合公报与三个联合声明,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既有框架,成功指引了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而如今,这个框架不足以引领从今往后的中美关系。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三个公报主要处理的是台湾问题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问题。而今天除了台湾问题之外,中美之间还遇到朝核、南海、全球经济治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没有体现。在坚持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个联合声明总原则下,还要继续寻找新的框架进行补充,这样才能指引中美关系更加均衡的发展。至于是不是要叫第四个联合公报或者别的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一些应对新问题、解决新矛盾的新框架。
1972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正式签订。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些新框架要包括什么要素呢?
袁鹏:首先,要对世界基本潮流形成共识,这也是三个联合公报的经验。公报开篇即是双方对世界局势的总括描述。而当前,双方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反差:比如,我们支持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而现在特朗普反全球化;比如说,我们倡导多极化,美国还是希望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这肯定不利于中美两国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形成共识。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社会化这些潮流方面,双方应该形成一些大的共识。
第二,美国要客观务实看待中美双方彼此力量的演变,进而承认中国是一个利益攸关方,接纳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也要让美国放心,中国的崛起不以挑战美国的霸权为代价。我们是跟自己比,并不是要超越和取代谁。即使经济上超越,我们也不想谋求霸权地位,双方需要一个再保证。
最后,就是对双方关注的问题划一条底线,找到趋向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径。
澎湃新闻:您对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进”怎么看?
袁鹏: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基辛格的共同演进思想是最具创造力和最具建设性的。不求双方走到一条路上去,但求双方水涨船高,你发展我也发展。至于演进到什么程度,需要双方在演进的过程中摸索和探讨。他另一重思想,是中美合作在冷战时期是基于共同威胁,冷战后是基于共同利益,今后要基于应对共同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借鉴。
澎湃新闻:您认为基辛格的观点得到美国战略界普遍认可了吗?
袁鹏:美国战略界思考中美关系大战略的并不多,有点青黄不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年轻一代过于学究气,而现实主义培养出来的一批学者又过于咄咄逼人。怎么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既理性,又具备经验和历史记忆,同时善于从人类的整体关怀来思考问题,这样的人物确实比较少见。像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今天从中国领导人嘴里说出来,得到世界的认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以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方法去思考问题,而现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在美国还是比较稀缺。
这一问题的产生与美国国内过度追求学术专业化,关注问题越来越细分有一定关系。对中美关系进行通盘研究的学者群体这些年在减少。我认为还是要弥补细分研究与整体研究的鸿沟,否则会影响美国战略界的整体对华战略思维。
澎湃新闻: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似乎并未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
袁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状态发生了变化,必须用新的思路去破解,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并不代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统摄了中国整体对外关系。与此同时,中俄之间还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这些双边关系为基础,我们还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如果新型国际关系运行顺畅,我们最终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相互补充和层层递进的思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范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与其他设想是相互补充的。应该说,美方对此概念一开始是有呼应的,但对其中“相互尊重”这一条则有所保留。但后来各种事态的发展导致美方将其束之高阁。但我认为只要我们持之以恒、言行一致地去推动,还是有希望的。
澎湃新闻:有美国专家提到,中国喜欢谈论抽象大框架而不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美国更期待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如何弥补这种差异?
袁鹏:美国人一听中国人谈大框架就头疼,他们希望就事论事,通过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去累积互信,进而构成框架。我们习惯先搭建一个框架,在框架内解决问题。我们并非搭建了框架就不解决问题,而是我们认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需要一个框架做引领。我们两个国家不是一般的国家,是超级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具体议题去推动,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又出现了。因此,中国一贯强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需要构建一个框架。今后,应该互相向对方的路径靠拢,两国智库之间也应该多交流,彼此取长补短。
澎湃新闻:您曾经提到过,您工作的现代院与美国智库一道讨论,建立“跨太平洋框架”,主张通过中美双边投资谈判等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在当前美国频频掀起“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
袁鹏:中美之间的路子走不通也得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否则双方只能陷入冷战或者热战,双方和世界都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尽管目前呈现出了特朗普掀起“贸易战”的局面,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中美关系往前走的一个逆流和插曲。目前,同意他打贸易战的人也不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两国经贸利益已经深度交织。因此只能坐下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与合作来破解,任何单边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特朗普这样一种做法,给双方建构合作框架造成一定冲击。但我想随着后特朗普时代的来临,包括特朗普本人经过反思后,会回到就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和沟通的轨道上。届时,我们可以就双边投资谈判、如何在太平洋地区和平共处的制度安排等问题进行谈判。一步到位很难,我们先从东北亚的和平机制开始,从南海相互规避冲突谈起,一步一步形成亚太和平共处的制度性安排。